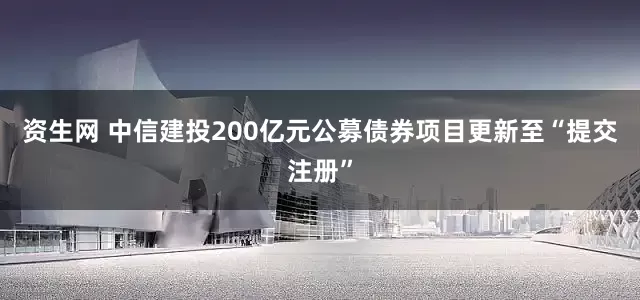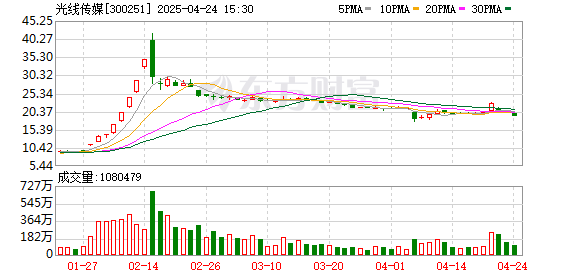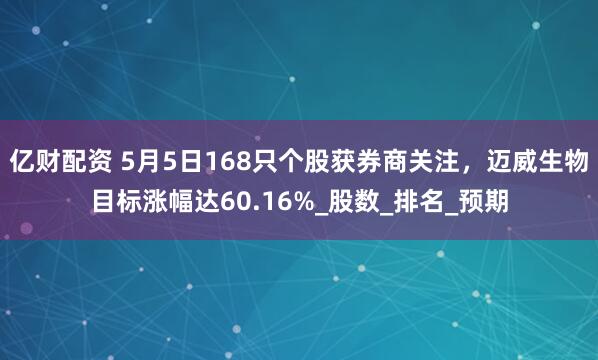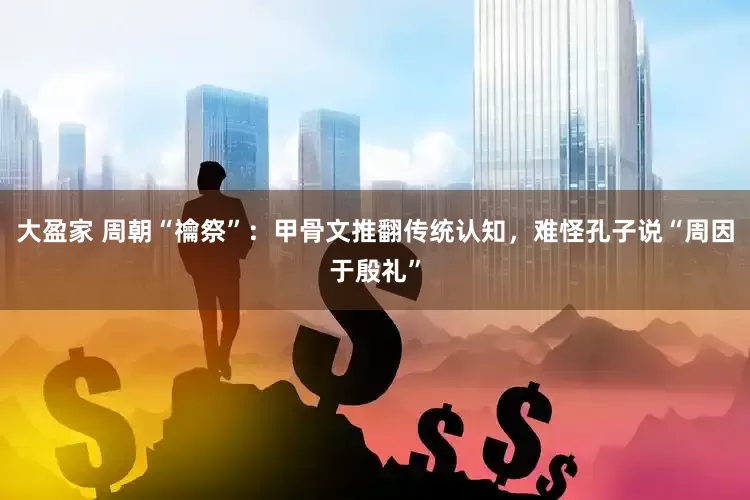
周易记载:“九五:东邻杀牛,不如西邻之禴祭,实受其福。”其中,所谓“东邻”是指纣王商人,“西邻”是指姬昌周人大盈家,问题是“禴(yuè)祭”是什么意思呢?
对此,秦汉以来的解释认为禴祭为“薄祭”,因为“文王俭以恤民”而崇德,祭祀时不注重外在形式,不使用贵重的“牛牲”,而使用“豕牲”,于是认为“故既济九五,不如西邻之禴祭,九五坎为豕,然则禴用豕而已”,就是虽然商人祭品贵重,但效果不如周人诚信诚德的薄祭。
《逸周书·世俘》记载:武王克商之后,庆典祭祀仪式上“籥人”(禴通籥、龠,其中禴的偏旁示为祭台)专职负责“籥祭”参与国家祀典,甚至其中还有“若翼日辛亥,祀于位,用籥于天位”。总之,世俘显示禴祭是周人极其重要的一种祭祀方式。
因为“禴祭”的重要地位,又因周人崇德薄祭,于是就出现了一个观点,即以王国维为代表提出“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、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”的观点,就是周人废除商朝制度、重新建立新的制度,强调两者之间传承不多,或者说废大于继承。
展开剩余83%但问题是:弃旧立新的观点,却与孔子观点相悖,因为孔子明确说过“殷因于夏礼,所损益,可知也;周因于殷礼,所损益,可知也”,孔子强调的是商周制度“虽有小异,实属大同”,两者之间传承没有断绝,那么商周制度究竟怎么,孔子正确、还是王国维正确呢?对此,甲骨文中的“禴祭”就已经给出了回答。
古中的禴为一种乐器按照秦汉之后古人解释大盈家,禴祭属于礿祭的别称,两者属于同一种祭祀。比如,汉朝王充《论衡·祀义》中说“ 纣杀牛祭,不致其礼;文王礿祭,竭尽其敬”,描述的就是“东邻杀牛,不如西邻之禴祭”,只不过将其中的“禴祭”换成了“礿祭”。
所谓“礿祭”,是古代宗庙的祭名,属于“时祭”,祭祀时间有春季、夏季等不同的说法。因为祭祀时间固定于或春或夏的缘故,当时物产不多,于是只能使用薄物祭祀。同时“礿”读音也为“yuè”,与“禴”读音一样。
问题在于:两者到底是不是同一种祭祀呢?其实,古书对禴与礿的记载表明,两者应该不是一种祭祀方式。
许慎《说文解字·龠部》记载:“龠,乐之竹管,三孔以和众声也,从品仑(见下图)。”还有,《乐书》记载:“古之人始作乐器,而苇龠居其先焉。震为六子之首,龠为众乐之先。”总之,古书中的“龠”是一种管乐,至于直吹还是横吹难以考证。
与之通假的“籥”,史书也明确记载为乐器,比如礼记中说“苇籥,伊耆氏之乐也”,诗经中说“籥舞笙鼓”,孟子中说“管籥之音”等。“禴”与“籥”、“龠”通假,旁边多了一个“示”字部,相当于在祭台旁奏“龠”。至于“礿”,古人也不知道文字来源,但汉代郑玄考据,该祭礼与农作物初熟相关。
也就是说,禴祭之“禴”是一种管状乐器,禴祭应与音乐相关,而礿祭属于固定时间的“时祭”大盈家,没有证据表明其与音乐相关,且音乐与时节没有固定联系的必然性。禴祭或因注重音乐而减少祭祀牺牲,最终表现出“薄祭”,但只是“可能”,因此两者应该不是一种祭祀方式,更重要的是甲骨文证明古人混淆了彼此。
甲骨文推翻传统认知古本《竹书纪年》记载:帝辛六年,“西伯初禴于毕”。其中之“初”,指姬昌首次使用“禴祭”,是在“毕”这个地方。那么,“禴祭”是不是姬昌或周人发明的呢?答案当然不是,因为甲骨文中早已有了禴祭,且还有礿祭。
首先,甲骨文中的“龠”,是编管乐器的象形,比如学者徐中舒指出“卜辞用为祭名,盖用乐以祭也,后世增示作禴。”除了徐中舒,郭沫若、董作宾等都认为是管乐。没有找到“龠”的适合图片,下图不像,应是排箫类的,甲骨文“龠”正常写法比上文西周“仑”字多了三“口”。
其次大盈家,甲骨文中多处使用“龠祭”,比如“戊戍卜,口贞:王宾仲丁彡龠,亡旧。十月。一”。其中“彡龠”,董作宾考证认为是“彡为鼓乐之祀”。
第三,学者夏虞南的“以“禴祭”为中心看殷周礼制转向”论文,对比了“世俘”中“禴祭”与商朝“龠祭”,指出武王克商所用之“禴祭”:“无论是时间规律还是礼仪形式上皆与卜辞所见‘龠’、‘彡龠’相同”。综合考证周朝禴祭之礼后指出:“以‘禴祭’为代表的周初礼仪,几乎全盘继承殷人祭祖礼仪的名称。”
当然,随着周朝统治的稳固,随着时间的推移,以及商周认识的差别,周朝最终在商朝制度上发展出了一套礼乐制度,也就是孔子所说的“周因于殷礼,所损益”。比如,商朝人祭、厚祀的传统被慢慢淡化了。
除了“禴祭”之外,甲骨文中也有“礿祭”,学者张俊成《甲骨文金文中所见商周礿祭》论文已有详细研究,指出“礿祭”是在宗庙内祭祀,对象是先王先公等,祭品非常丰厚,没有确定的时间,但主要集中在春秋两季,这就推翻了郑玄的商代“春祭曰礿”。西周金文显示,当时对商朝“礿祭”依然有所继承,真正固定变成四时祭祀之一的是在战国时代。总之,禴祭与礿祭本是两种祭祀,的确是秦汉之后古人将之混淆了。
因此,从禴祭来看,孔子所说的“周因于殷礼,所损益,可知也”是正确的,周朝的确继承了商朝制度,即周承商制,而不是简单的弃旧立新。我们说中华文明没有断绝,这些也是铁证之一。
最后,关于本文话题,还有两点值得一谈:
首先,禴祭本质上是一种乐祭,而从周初开始就非常重视禴祭,比如“用籥于天位”,可见周朝礼乐制度之“乐”,显然与之相关,应是对商朝禴祭的继承和发展。相比商朝,周朝更注重音乐通神,所以考古也发现很多青铜乐器。
其次,上文孔子所说的话,其实还有更厉害的下半句,即“其或继周者,虽百世(一世30年,百世3000年),可知也。”也就是说,孔子了解中华文明特性,知道中华文明不会断绝,虽过3000年,虽周朝或已不在,但新王朝会“有损益”的继承下去。如今事实证明,孔子所言正确。
发布于:江苏省可盈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